【卢春红】从“感情”到“自由的愉悦”:18世纪西方美学视域下的情感探索
如果说趣味问题是近代西方思想构建美学学科的引线,那么18世纪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不再限于对趣味能力的个体教化与培育,而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与主体自身的感性相关联,探索趣味问题在主体自身的先天能力与普遍性依据。在由此而来的理论推进中,康德以共通感为先天条件来解说“愉快和不快”的情感,不仅对主体之情感状态做出先验解说,而且将审美情感的品性指向“自由的愉悦”。然而,从18世纪西方美学的整体背景反观,将共通感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情感其实是多重思路交错下的结果。在对情感之先天条件的探寻中,美学视域之外的探索路径首先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美学的学科建构带来复杂影响。不过,恰恰是在这一远离而又回复的过程中,共通感作为先天条件与主观原则的意义彰显,并使得“愉悦”的自由品性发生重要转化。本文尝试以情感这一审美感受的主体条件为引线,呈现其在18世纪思想背景下的探索过程,阐明共通感进入美学学科的思想背景以及它对情感呈现产生的影响。
一、由“感官”到“情感”:审美感受的主体条件
作为现代美学的开启者,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ftesbury)的理论探索在英国思想世界中有着复杂的面相。从近代以来经验论的总体脉络来看,其奠基者培根明确反对虚幻的想象和空洞的推理,要求从对外部经验的观察中获得知识的来源,作为集大成者的洛克更是强调心灵的白板说,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当霍布斯将这一思路引入人类事务,以自然状态为理论前提论证国家的产生时,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本质亦随之显露。与此相比较,夏夫兹博里的理论探索显示出学术旨趣的差异。在其陆续写于1699——1710年间风格各异的三卷本《论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中,他对社会事务中公共利益问题的关注占据核心位置。将这一思路与人性的建构相关联,从对公共利益的诉求指向对人的社会品性的培育时,夏夫兹博里在道德趣味的建构中意识到审美趣味的重要性,其建立在无利害性原则上的审美观念也因此奠定了现代美学思想的基础。1790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探究“鉴赏”在主体自身的先天条件时,“无利害性”原则依旧构成分析鉴赏判断的前提条件。

[英]夏夫兹博里:《论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
不过,将夏夫兹博里的这一观念仅仅理解为对外在功利目的的排除,远不能揭示出其理论探索的深层意义。从情感的角度切入,夏夫兹博里的关注重心,固然是对人的品性的经验性培育,更是对建构这一品性的心灵基础的阐明。在以“无利害性”排除霍布斯利己主义人性观的同时,夏夫兹博里的探索路径并未停留于公共利益,而是将呈现这一利益的依据与主体自身的内在感受相关联,并赋予这一情感状态以重要地位,认为“在一个理智的生物来说,完全没有通过任何感情(affection)而变得成熟,是不会对那种生物的本性的善或恶造成影响的;只有当与他有关的系统的善或恶,是触动其情感(passion)或感情(affection)的直接对象时,他才能被假定为是好的”。
在这一意义上,认为夏夫兹博里的转向受到英国这一时期与经验主义分庭抗礼的剑桥柏拉图学派的影响,固然其依据,二者确乎显示出方向上的趋同性,即在现实世界呈现精神性的存在,不过,将这一探索最终落实于主体的情感状态,表明夏夫兹博里承载的是经验主义的内核。在强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时,他依旧将这一社会关切的标准以及起源置于主体的感性状态中,这显然是经验论前辈探究问题的主导模式。对于人的观念的起源,经验论不同于唯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以主体自身的感觉为出发点对其作出解说。在成书于1651年的《利维坦》中,霍布斯首先表现出明确意向,认为“人类心里的概念没有一种不是首先全部或部分地对感觉器官发生作用时产生的”。洛克在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中重新审视这一主题时,虽然不再将感觉作为观念的唯一来源,但仍然肯定了与感官对象相关的感觉“是观念的一个来源”。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主体的这一感性状态?面对心灵的内在状态,霍布斯的特殊之处在于将感觉与生命的“自觉运动”(voluntary motion)直接相关,认为这一感受虽是“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事物的作用引起”,在本质上呈现的却是“人类身体的器官和内在部分中的运动”,也由此与这一自觉运动在其最初阶段的内在开端即 欲望产生关联。因为“人体中这种运动的微小开端,在没有表现为行走、说话、挥击等等可见的动作以前,一般称之为意向。当这种意向是朝向引起它的某种事物时,就称为欲望或愿望。……当意向避离某种事物时,一般就称之为嫌恶”。同样面对主体感受状态,洛克则在感觉之外还补充了另一种心理状态——“反省”。感觉的目的是与外部事物产生关联,反省的目的则是让“我们还知觉到自己有各种心理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反省”并不单纯是与“感觉”相并列的另一种心理状态,作为一种“后起的”、以“知觉”方式呈现的状态,它还与心理的“快乐与痛苦”产生关联,呈现出快乐或痛苦的知觉。由此,当洛克强调“如果我们一切外面的感觉同内在的思想,完全和快乐无涉,则我们便没有理由,来爱此种思想或行动而不爱彼种,或宁爱忽略而不爱注意,或宁爱运动而不爱静止”,表明的则是感觉与情感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在这一意义上,指出夏夫兹博里与霍布斯思想中利己与利他的区分只是表层,更深层的差异在于二者面对主体感受状态时的不同方向。与霍布斯将这一感性存在与欲望能力相关联不同,夏夫兹博里通过“无利害性”观念,在排除私人利害的同时,也剥离了感觉与欲望的关联,并在客观上接纳了洛克的思路——将心理感受与情感相关联。如果说在洛克的论说中,情感还只是与感觉状态相伴随的另一个因素,夏夫兹博里则直接将主体的感性状态称作感情,并集中考察了“哪些感情是好的和自然的,哪些又是坏的和反常的”。在1728年的《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一书中,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正是沿着夏夫兹博里所开启的探索方向,将感情或激情进一步界定为与感觉不同的另一种“快乐或痛苦的知觉,它们并不直接由事件或对象的出现或运行引起,而是由对它们当下或确定性的未来存在的反思或理解而产生,因而确信该对象或事件将会使我们产生直接的感觉”。

[英]弗兰西斯·哈奇森:《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
不过,哈奇森并未停留于对情感状态的单纯描述,而是进一步探寻与这一状态相关的主体能力,并把由这一能力而形成的“规定”指向“感官”,以便为感性状态提供主体自身的依据。将与美的感受相关联的主体能力指向“内在感官”(internal sense),是对这一探索路径的实质性推进。反观《论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中的论述,夏夫兹博里也曾将情感状态的主体依据指向“内在的眼睛”。相比之下,哈奇森的解说更为明晰,不仅确定了这一能力的感性身份,而且以“内在”方式与外在感官相区分。这倒不是说,“内在感官”是哈奇森首次使用的术语。早在《人类理解论》中,伴随对观念之起源的分析,洛克就通过“反省”这一特殊心理状态发现主体自身存在一些特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是人人完全在其自身所有的;它虽然不同感官一样,与外物发生了关系,可是它和感官极相似,所以亦正可以称为内在的感官”。在承接洛克的这一概念时,哈奇森的推进之处在于,在将内在感官明确与审美感受相关联时,扭转了这一感官的主要内涵,指向的不再只是心灵的一种内在状态,而是主体自身的情感状态。在哈奇森对“感官”概念的总体界定中,这一倾向得到集中体现:“如果把可以接受独立于我们意志的观念、并产生快乐或痛苦知觉的心灵中的每一种都规定称为一种感官,与通常解释过的那些感官相比,我们将发现许多其他感官。”这里,“其他感官”指向的正是除外在感官之外的“内在感官”,而后者的特点则在于通过规定与情感状态相关联。
然而,将审美感受的主体能力称作内在感官,虽显示的是与“外在感官”的区分,却也暗示着其尚未摆脱对“感官”的某种依赖以及与外物的纠缠。这表明,主体的感性能力若要真正呈现其作为情感的本色,尚须走出“内在感官”的表述方式。在这一意义上,休谟的解说路径显示出理论探索的另一层推进。1739——1740年出版的三卷本《人性论》中,休谟在主标题下还加了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以表明这部著作的总体研究路径是:将科学的方法引入精神领域,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呈现人性的本质。正是通过引入新的方法来剖析“人性”,年轻的思想家与其经验论前辈产生了切入点的差异。依据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论述,心灵中“观念”(idea)的起源被指向两个相关而不同的途径:“感觉”(sensation)与“反省”(reflection)。其中,通过感觉所关联的感官,观念的对象指向外部事物;通过反省,观念的对象指向主体的心理活动。同样面对知识的起源,休谟则将探究主体的切入点指向“知觉”(perception),认为“不通过一个意象或知觉作为媒介,任何外界对象都不能被心灵直接认知”。但这并非是说,主体心灵的感受状态由“感觉”转换为“知觉”,而是说知觉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洛克认为,由于“人心只有在接受印象时,才能发生知觉”,因而知觉作为“人心运用观念的第一种能力”,是“我们反省之后所得到的最初而最简单的一种观念”。休谟却颠倒了二者之关系,强调“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物就是知觉”,无论是印象(impression),还是观念,二者作为主体的心理状态均由知觉所呈现。
休谟之所以赋予“知觉”以重要地位,源于探索思路的根本转向。洛克虽将观念的来源区分为两种,却认为感觉的对象是观念的首要来源,而主体自身的心理活动是“我们在运用理解以考察它所获得的那些观念时”才知觉到的,目的是将观念的来源最终指向外部经验。休谟则认为,“印象”作为“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烈的那些知觉”,虽也可以区分为“感觉”与“反省”两种,然而,且不说反省印象“大部分是由我们的观念得来”,即使是感觉印象,也是“由我们所不知的原因开始产生于心中”,二者均明确切断了感觉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将这一解说理解为休谟对主体能力分析的精细化,并未准确捕捉到其在主导思路上的变化。认为感觉可以通向经验,其实是反向指出,我们需要通过外部经验来论证感觉的存在。在17——18世纪英国经验论的证明思路中,感觉虽构成基础要素,却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性,通过与外部对象的直接关联正可为这一主体感受提供现实化路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知觉不与外部对象直接相关,这一点早在洛克将知觉归于“反省”方式时就已显示出来。休谟通过摆脱“反省”路径,直面“知觉”,不仅揭示出这一概念的独立性,而且彰显其对于心理感受的重要性:从主体的视角来看,心理的感受本质上是经由主体知觉来获得自身的呈现。
但这并非是说,通过摆脱与外部经验的关联,休谟远离了经验论的探索路径。在将精神落实为个体化存在的唯理论探索模式中,莱布尼茨也从“知觉”切入来分析单子这一精神个体的内涵,让知觉呈现为从微知觉到统觉逐渐明晰化的过程,从而解决了感觉与思维之间的过渡问题。本质上讲,这并非感觉与知觉单纯消弭界限式的混同,而是让个体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以便知觉的不同存在状态都建立于思维的基础之上。与此相比较,休谟采纳的是全然属于经验论体系的感性视角。他虽也将知觉中观念与印象的差别归结为“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各不相同”,但这一不同是感性因素之间的差别。因为观念在本质上归属于知觉,它们即使会与思维有关联,也只是“用来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在这一意义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在1710年的《人类知识原理》中强调,我们思想、情感和想象所构成的观念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epi)”,只是对这一思路的开启,当休谟进一步甩掉贝克莱将知识起源指向上帝的精神依赖,才真正完成知觉的主体化呈现。

[英]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
在这一意义上,当休谟认为自己在解说人性的原理时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全新的基础”指向的正是主体化的方向。在近代思想的发展中,彻底主体化的方式对于感性能力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如果说让观念属于知觉,并由此消除感性与理性的关联,是让康德的先验哲学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的重要契机,那么将感觉与外部事物的关联彻底切断,才是隐藏在思想探索底层的真正创见。一旦外部经验不再是感觉现实化需要凭借的客观依据,就意味着“感觉”可以借助于感官,却不必依赖于感官。在“感官”(sense)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的同时,感觉与其他主体感性能力相关联的可能性得以呈现。在将关注重心转向内在感官时,哈奇森虽已显示出对“知觉”的关注,并将与感官相关的感性状态称作“感官知觉”或“内在意识知觉”,然而,如果这一感官尚未摆脱与外在事物的关联,知觉便无从彰显自身的重要性。这构成了休谟与哈奇森思想的核心差异。在从感性角度来探究普遍性的根源时,哈奇森的“内在感官”如同“共同感”“道德感”“荣誉感”一样,本质上已与感官感受无直接关联,将其归结为“感官”,即使是以“类比”方式,也掩盖了这一感性能力中本应呈现的真实内涵。而以知觉作为分析人性的切入点,休谟学说中的主体感受能力在排除外在因素的纠葛后,也将自身作为情感的本色呈现。在知觉中,不仅“印象”作为“心灵中最强最猛的”部分,内含的是“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而且“观念”以“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的方式也被归属于感觉、情感和情绪等心理状态。
统观休谟对于人性中三个部分的解说,情感部分占据了该部著作的一个独立章节。在以名为“情感”(passion)的专题方式对这一主体能力给予关注时,休谟的论述范围虽未局限于审美领域,却不影响这一能力在人性中的特殊地位。即使在分析道德情感时,休谟对“道德感”的术语使用也做了并非无关紧要的调整——由“moralsense”调整为更为常用的“moral feeling”或“moral sentiment”。周晓亮在《休谟哲学研究》一书中对这一调整给出推测性解释,认为“这也许是由于休谟不希望人们简单地将道德感当成与肉体感觉完全相同,因为自从道德感理论提出,关于是否能发现像眼、耳等外部感官那样的道德感官,就成为对道德感理论的主要责难之一,所以休谟在用词上突出道德感的情绪、情感的特点”。显然,这一推测主要侧重于道德论证的视角,但也不妨碍以此为切入路径,呈现其中内含的由感官向着情感的转向。1757年,在专题研究论文《论趣味的标准》中,休谟通过对理想的批评家的分析指出了趣味能力的标准,即“有健全的理智力,能同精致的情感相结合,因为锻炼而得到增进,通过进行比较而得以完善,还能清除一切偏见。只有批评家才有资格拥有这些宝贵的品质,这样的共同裁决,无论在什么地方被发现,都是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这里,“健全的理智力”与“精致的情感”虽然还存在术语内涵上的纠缠,作为趣味之主体能力的情感包含这两个方面的要素则是明确的结论。
在开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先验哲学的建构中,当康德通过一种新的判断力来强调审美判断的主观化倾向时,他承接的依旧是休谟的这一转向,并特意指出,“如果对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的一种规定被称为感觉(Empfindung),那么,这一表述就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于我在把一件事物的(通过感官,即一种属于认识能力的感受性而来的)表象称为感觉时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强调“用情感这个通常流行的名称来称谓任何时候都必定仅仅保持为主观的、绝对不可能构成一个对象的表象的那种东西”,这并不单纯是具体术语使用上的调整,而是主体感受能力在美学视域下的呈现。
二、普遍性解说的非审美指向:两条情感探索路径的分立
在对趣味之主体根源的探究中,从“感官”到“情感”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环节。真正说来,主体自身的现实感受状态并非单纯官感,而是感觉与情状相结合的情感。将其首先指向“感官”,内含的其实是尚未与外物相剥离的原初状态。一旦采用彻底主体化方式,情感作为审美感受之主体条件的本色便得以彰显。不过,探究审美感受的主体能力,呈现这一能力的独立品格只是基础环节,其最终目的则是给美学学科的建构提供普遍性保证。这意味着,对情感之独立性的彰显同时伴随着对这一能力的普遍性探求。
早在夏夫兹博里从主体的感性状态切入对趣味的分析时,阐明其在心灵中的情感条件,同时也是为了对这一感性状态的普遍性质进行解说。面对主体自身的情感感受,夏夫兹博里首先将其分为三种不同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自然感情,导致公众的善”,第二种状态是“自我感情,仅导致个体的善”,第三种状态表现为“两者都不是,并不导致公众的或个体的善,而是恰恰相反;因而可被叫做非自然感情”。由对这些情感状态的分析可知,夏夫兹博里并不否认自我意义上的感情,这一感情虽从个体出发,最终指向的却是“善”,因而与自然感情所关联的“善”呈现出方向上的一致性。需要关注的是自然感情与非自然感情之间的关系。以强化的方式呈现二者之间的对执,意图表明的是自然感情与非自然感情在根本上的不兼容。在这一意义上,想要将对人的社会品性的培育指向“公共的善”,与普遍意义上的感情相关联,排除非自然意义上的感情构成基本前提。此后的哈奇森也明确指出,“在我们称为高尚的这些感情(affections)中,没有哪一种会源于自爱或对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的欲求”,而是存在于“排除了自我利益”的“仁爱之爱”中。为了进一步说明作为“无私的仁爱”的情感来源,他也将其与道德感官相关联,并对这一来自夏夫兹博里的概念做了系统论述。

[英]托马斯·里德:《论人的理智能力》
然而,也正是在将情感能力的解说与普遍性的追问相关联时,经验论探索路径中内含的美善不分的状况随之显出。在夏夫兹博里的论说中,普遍意义的情感被明确指向“公共的善”。哈奇森虽将“内在感官”与审美感受相关联,并用这一主体能力来标识“令人愉快的知觉”,其与“道德感官”之间的界限依旧不清晰。如果五官感受因其与外部事物相关联而被看作是“外在感官”,那么“道德感官”同样可归属于内在感官。在1785年问世的《论人的理智能力》一书中,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创始者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就直接指出,“格拉斯哥的哈奇森博士认为,我们具有的简单、原始观念不能归功于外部感官或意识,因此他引入了其他的内部感官,比如和谐感官、美感官和道德感官”。究其根本,美与善的纠葛固然意味着对美之为美的普遍性探究需要以对善的解说为前提,但同样伴随其中的另一种潜在倾向则是:以分析道德情感的路径来解说美学意义上的情感能力。
这一倾向在休谟彻底主体化的路径中以分立的方式凸显。值得关注的是,在对情感能力的解说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同情”出现在休谟对情感内涵的分析中。在将道德感作为道德区分的依据时,休谟给予重要补充:“同情(sympathy)是道德区别的主要源泉。”人们常常容易在与怜悯相关的意义上来理解同情,因为怜悯是同情呈现自身内涵的主要方式。从其本质而言,二者却有着很大不同。听闻他人的不幸遭遇,人们难免悲伤,在这一情境中,“怜悯”(pity)作为“对他人苦难的一种关切”,其着眼点在遭遇不幸时的具体状况。与此相比较,同情则着重凸显的是情感之间相互传递的性质。休谟为此特意强调,“在同情现象方面,心灵很容易由‘我们自己’的观念转到和我们相关的其他任何对象的观念”,以表明在同情的感受中,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实际状况——虽然这一感受并未离开这一状况,而是心灵之间的转换与传递。更关键的是,同情与怜悯不只是关注重心上的差异,前者还从根本上构成后者的基础:正是因为情感可以相互传递,人们才能对他人的不同境况做出应答。从道德论证的角度,将对“道德感官”的探究转向对“同情”概念的分析无疑是休谟在理论上的推进。从审美视角下关注这一情感探索,随着情感能力的明晰化,彰显的却是知觉与同情的分立。与在道德领域中将同情作为道德区分之来源相对照,在知识领域中,知觉则占据了核心位置,不仅与感觉相关联的印象由知觉而来,而且与思维和推理有关的观念之来源也与知觉相关。如果说在哈奇森的理论探究中,知觉与感情还共同出现于这一情感能力中,因为知觉总是伴随着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那么在对“人性”做科学的探究时,恰恰因为纯粹的主体化,剥离外在的干扰后,情感探索中两个因素的分立也随之彰显。
两条探索路径的分立也可从休谟对价值与知识之差异的描述中得到印证。在《人性论》道德学部分的一个附论中,休谟针对道德学说给出一段补充说明:“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在这段被后来研究者认为是著名的“休谟的法则”(Hume's Law)的表述中,休谟指出了存在于推理中的两种不同关系:一种是“是”与“不是”的关系,一种是“应该”与“不应该”的关系。以往的道德理论从“是”判断直接过渡到“应该”判断,而在休谟看来,问题正是在这一未经证明的过渡中,因为从“是”判断推断不出“应该”判断。落实于情感能力的探究,尝试将主体感性能力中的知觉与同情区分开来,便是这一主导思路的体现。在对趣味评判标准的分析中,趣味所必需的两种要素——“健全的理智力”与“精致的情感”未能在主体层面呈现为一种感性能力,想必与休谟的这一关注视角有一定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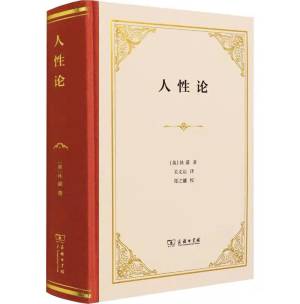
[英]休谟:《人性论》
面对心灵的诸种能力,康德也同休谟一样强调了知识与道德的差异,并将对两个领域的区分作为批判哲学的核心任务。不同之处在于,休谟的区分基于主体的感性能力,使用的是经验心理学的描述方法,康德的区分以理性为依据,采纳的是先验逻辑的解说模式。为了限制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康德将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前者为知识提供规则,指向自然领域;后者为道德提供法则,指向自由领域。将这一判定依据与情感能力相关联,其内涵中的两个不同层面也由此被区分为“感性直观”与“道德情感”。
人们通常接受一种未经审视的看法,认为在情感能力中这两个要素并不必然相关。然而,如果关注重心不是知识之可能,而是人性的真实感受状态,以“表象”方式呈现的感受过程很难剥离掉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从经验论一开始,这一点就被发现和描述,在通过感觉与反省来呈现心理感受时,洛克明确指出“快乐和痛苦——喜乐或不快几乎同一切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是分不开的”,因为“感官由外面所受的任何刺激,人心在内面所发的任何思想,几乎没有一种不能给我们产生出快乐或痛苦来”。在面对情感现象时,康德也认可了情感与其他感受的关联性:“与欲求或憎恶相结合的,任何时候都是愉快或者不快,人们把对它们的感受性称为情感;但并不总是反过来说。因为可能有一种愉快,它根本不与对对象的欲求,而是已经与人们关于一个对象所形成的纯然表象(表象的客体存在与否都无所谓)相联结。”在这一表述里,康德从一明一暗两个层面,既肯定了情感与欲望的结合,也认可了情感与表象之间的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探索路径的分立虽是美学意义上的情感尚未获得独立性认可的结果,更体现为探索感性能力的普遍性时有意识的选择。为获得普遍意义上的情感,18世纪的思想世界首先选择以两个因素分立的方式来探寻普遍性解说。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曾有过如下陈述:“为了区分某种东西是不是美的,我们不是通过知性把表象与客体相联系以达成知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与知性相结合)把表象与主体及其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相联系。因此,鉴赏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因而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人们把它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规定根据只能是主观的。”这固然是为了表明,将表象与情感相关联是阐明“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得以可能的前提,将其作为审美领域先天综合判断的核心任务也意味着,两种感性能力的分离是之前进行普遍性追问的基本条件。
顺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思路,探索路径的分立被明晰化的同时,普遍性的解说也随之呈现。从“表象”角度,分离的条件如上所述,即“通过知性把表象与客体相联系”。对这一路径的剖析集中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休谟对知觉的心理联想的分析证明,经验心理学的路径并不能获得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保证,康德则通过由理性提供来源的范畴(纯粹知性概念)来阐明先天意义的感性能力。在解说认识能力之可能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不仅从感性直观中剥离出纯粹的直观形式——时空表象,而且通过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和统觉的先验统一,在纯粹知性能力的规范中获得这一直观形式的先天性保证。从“情感”角度,分离的条件则是通过理性将情感与客体相联系,目的是获得情感的普遍性——可被先天认识的情感。休谟对情感之同情原则的解说,虽提供出“旁观者”的立场,显示出与他者的关联,但“可传达性”的呈现依旧基于经验性解说。康德则明确将情感与理性相关联,以理性来规定情感。在对道德法则之可能的主观原则的阐明中,康德不仅剥除了由情感对感性欲望的依赖而来的偏好,而且在情感对道德的兴趣中阐明了这一先天情感的内涵——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并通过让主观原则同时成为客观原则,保证了这一情感的先天性。
然而,从美学学科的角度反观这一过程,分离式解说作为必要路径,固然让其中的要素以各自独立的方式获得普遍性,成为先天意义上的感性能力,却也给学科的建构带来问题。在休谟的论述中,探索过程因其经验论底色,强调从感性视角追问观念的起源,从而掩盖了分立对美学建构的影响。在将这一过程置于先验哲学体系后,康德的解说不仅以醒目方式强化了两种探索路径的区分,而且呈现出美学学科由此而来的现实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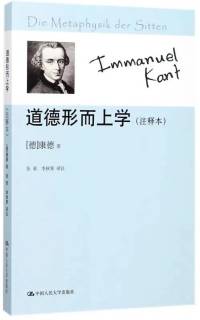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
首先,在对认识领域中的感性能力进行分析时,康德在将其置于先验感性论(Die transzendentale Ästhetik)的同时,也在第一节的注中表达了对Ästhetik的明确态度:“惟有德国人如今在用感性论这个词来表示别人叫做鉴赏力批判的东西。在此,作为基础的是杰出的分析家鲍姆加登所持有的一种不适当的希望,即把对美的批判性判断置于理性原则之下,并把这种判断的规则提升为科学。然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上述规则或者标准就其最主要的来源而言仅仅是经验性的,因而决不能充当我们的鉴赏判断必须遵循的确定的先天规律;毋宁说,鉴赏判断构成了那些规则的正确性的真正试金石。”显然,这里的Ästhetik已非古代思想中区分“αιδθητα χαι νοητα(可感觉的和可思想的)”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内含着由先验哲学体系而来的变化。就前者而言,“可感觉的”与“可思想的”是不相关联的独立存在,而在近代思想中,“Ästhetik”(感性论)与“Logik”(逻辑)彼此区分的前提是,二者同时含括“可感”与“可思”两个因素。在第一批判中,“Logik”作为主导性思维方式,同时肩负着对感性进行规范、使感性直观拥有普遍性的任务。这也意味着,当康德“部分地在先验的意义上、部分地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接受感性论(Ästhetik)”时,这一概念已显示出与鉴赏力之间的应有区分:正是Ästhetik成为使鉴赏能力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然而,为了感性能力在客观化意义上的先天性,康德否认了鲍姆加登在建立美学学科时将与鉴赏相关联的情感指向“Ästhetik”的思路,认为“把对美的批判性判断置于理性原则之下,并把这种判断的规则提升为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呈现鉴赏的主体情感能力是经验性的,构成鉴赏判断之基础的Ästhetik无法获得先天规律。在这一意义上,剥离感性表象与“主体及其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的关联,使其成为感性直观,同时内含着对作为逻辑基础的“Ästhetik”的排除。
其次,在对道德领域中的情感概念进行分析时,康德明确指出:“同甘和共苦(sympathia moralis[道德上的同情])虽然是对他人的快乐和痛苦状况的一种(因此可被称为审美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感性情感(同感、同情的感受),自然早已把对它们的易感性置入人心了。……现在,这种易感性可以被设定在就其情感而言互相传达的能力和意志之中,或者只是设定在对快乐或者痛苦的共同情感 (humanitas aesthetica[审美的人性])的易感性之中,这是自然本身所给予的。”这里,在面对“对他人的快乐和痛苦状况的一种愉快或者不快的感性情感”这一审美情感时,康德虽也为这一指向审美情感的“易感性”提供出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将“可传达性”与“意志”相关联,一种是将“可传达性”与“感性情感”相关联,却同时强调,前一种状态中的情感“是自由的,因此被称为同情性的(communio sentiendi liberalis[自由的感觉共联性]),基于实践理性”,后一种状态中的情感“是不自由的(communio sentiendi illiberalis,servilis[不自由的、奴性的感觉共联性]),可以叫做传达性的(例如热情或者传染性疾病的感觉),也叫共患难”。这并不单纯意味着,为了获得自由意义上的“同情性的”情感,我们需要放弃不自由意义上的“可传达性的”情感,更关键之处在于,为了获得自由意义上的“同情性的”情感,还需要排除构成这一情感之基础的Ästhetik路径,因为“同情”作为一种“感性情感”本就内含经由“审美的人性”(humanitas aesthetica)而来的Ästhetik基础。由此,“对快乐或者痛苦的共同情感”在经由理性的规定获得其在“同情”中的先天性时,这一情感也被剥离了与Ästhetik的关联。
概而言之,在情感能力的两个因素以各自方式获得自身的先天性时,审美意义上的Ästhetik以否定方式被剥离开来。由此,内含于休谟“是”与“应该”的区分中的美学效应在康德的先验解说中得以呈现:当情感通过理性规定而呈现自身的普遍性之时,这一规定同时意味着对情感内涵中不同要素的分离,而与审美状态相关联的情感正是在这一分离中消弥自身。
三、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何以指向共通感?
在18世纪的思想境域中,由对趣味能力的关注转向对情感状态的解说,目的并不只是对主体审美感受的呈现与描述,而是由此指向构成其来源的情感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情感能力之普遍性的探究是近代美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依托于理性,是近代西方思想综合考量的结果,只有借助与理性相关的路径,方可获得纯粹的普遍性。然而,回顾这一探索过程则会发现,以理性方式规定感性,固然能获得可被先天认识的诸感性能力,却无法解决美学自身的问题。更有甚者,当主体的感性能力以两种不同路径获得理性规定时,被同时剥离的恰恰是审美状态中的感性。不过,美学建构中的这一尴尬状况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主体内在感受层面出现的美善不分的状况,其实凸显出美学论域中的情感在根本上拥有一种综合的性质,一旦通过分立方式获得情感的普遍性,美的情感便无处现身。于是,也恰恰因为这一规定普遍性的方式,审美领域与道德、知识领域的真正差异彰显:美的情感并不是与知识、道德领域中的感性存在相并立的另一种感性状态,如果说“分立”构成前两个领域的前提条件,以“整体”方式来呈现自身则成为审美领域的内在诉求。由此,康德对共通感概念的关注呈现出重要意义。在1790年问世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从先验角度审视审美领域中的情感,即“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将这一情感能力的先天条件指向共通感,固然是因为后者在内涵上呈现出两条思路的交错,更在于其对审美领域而言的独立化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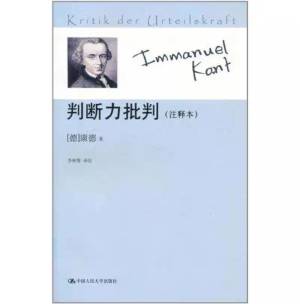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
回顾历史,首先可从词源学角度将共通感概念与两个重要思想传统相关联。一是古希腊时期,在分析“灵魂”的内在结构及其功能时,亚里士多德在与五官感觉相对照的意义上区分出一种在五官感觉之上的“共同感知”(koinê aisthêsis)概念,认为“对于能够被共同感知的事物,我们具有一种共同的感知能力,而且是并非偶然地拥有这一能力”;一是古罗马时期,通过将共通感概念与对于“公共福利和普遍利益的意识”相关联,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一概念指的“是对社群和社会的爱,是自然感情、仁善、责任感,或者那种来自对于人类的普遍权利的正确理解的文明礼仪,以及存在于人类中的自然的平等关系”。这两个传统也由此规定了共通感概念的基本内涵。即使到了18世纪,共通感成为主体心灵的感性能力后,其内涵仍然以两种不同的思路被推进。1711年,《论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第一卷第二篇文章曾以“共通感(common sense):论机智和幽默的自由”为题专门探讨了共通感概念。正是在这里,夏夫兹博里以书信体形式回溯并承接了古罗马人文主义传统,将这一概念指向在社会实践领域中具有可传达性的“共同的感情”。在出版于1785年的专著《论人的理智能力》中,托马斯·里德则发展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共通感概念作为普遍性感觉的内涵,将其指向一种与论证(argument)不同的“直觉的”(intuitive)判断,以此探究人类的心灵,并建立起获得知识的常识(common sense)原则。
纵观经验论路径关于共通感概念的解说,无论是对哪种传统的承接,均未显示出与审美领域的直接相关性。哈奇森在列举心灵的天然能力时,甚至明确将公共感官(common sense)看作是与审美的内在感官相并列的另一种感性能力,是“我们的决定会因他人的幸福而快乐,因他人的苦难而不快”的感官。其中的缘由在囿于感性状态的经验论描述中并不明朗,置于先验哲学的背景下,并阐明审美意义上的共通感概念后,康德则通过对照分析指出了共通感概念中的这两层内涵形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传统的实质。对于普遍感觉意义上的共通感概念,康德将其称作“逻辑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logicus),因为这一意义上的共通感实际指向的是“平常的人类知性”(der gemeine Menschenverstand),作为一种“健康的知性”,它在本质上并“不是按照情感,而是任何时候都按照概念,尽管通常只是按照被模糊地表象出来的原则来作判断的”。而对于共通感情意义上的共通感概念,康德将其也称作“道德共通感”(sens commun moralische),则是因为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被指向“道德情感”(das moralische Gefühl),它在先验的意义上同样是由道德法则所规定,是可被先天认识的情感,目的是让“主观原则”同时成为“客观原则”。
然而,也正是通过与共通感概念的两个传统内涵相对照,“审美共通感”的独特之处得以彰显。在《判断力批判》写作时期,康德将共通感接纳为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能力的先天条件,即可以在审美领域获得的先天意义上的情感,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些感觉而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认识能力的话,我们关于真理、合适、美和正义是永远不会想到这种方式的表象的”。这意味着,作为感性能力,共通感首先需要依托于更普遍的存在,才可能获得自身的存在,而后者同时也构成对普遍性的展示。由此需要面对的问题则是,在经由理性获得先天规定的同时,共通感如何保证自身的感性(审美)本色?从1781年的第一部批判哲学体系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到1790年《判断力批判》的正式出版,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看似山重水复,却也最终柳暗花明。当康德在1787年12月28日写给耶拿教授莱因霍尔德的信中宣称自己“试图发现第二种能力(愉快与不快的情感)的先天原则”时,这倒不是说康德找到了共通感这一先天条件。如果共通感概念一直存在于传统之中,那么康德真正发现的其实是将共通感解说为“先天条件”的新路径。

[德]康德:《康德书信百封》
顺着这一路径,康德对共通感概念做出如下富有特征性的解说:“人们必须把sensus communis[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说,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 (先天地)考虑到任何他人在思想中的表象方式,以便使自己的判断仿佛是依凭全部人类理性……”这里,将共通感首先理解为一种共同的 感觉的“理念”,强调的是这一概念的先天性维度,以“感性的”理念的方式作出限定则是意图彰显其作为先天条件的特殊性:一方面,想要获得普遍性,共通感须得与理性相关联,“依凭全部人类理性”;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评判能力”,共通感并不真正受理性规定,而只是“仿佛”依凭全部人类理性。换言之,康德通过“仿佛”两个字挑明了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需要理性参与其中,却又不能是概念化的规定。
为了呈现这一特殊的普遍性,康德尝试将共通感与一种以“反思”方式呈现的“评判能力”即反思性判断力相关联。如果说“判断力”是先验哲学体系中以逻辑方式呈现的核心概念,那么反思性判断力则是第三批判提出的新型逻辑,用来解决共通感概念如何呈现自身普遍性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共通感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这一评判能力,如康德所强调,“当可以察觉的不是判断力的反思(Reflexion),而毋宁说只是它的结果时,人们往往给判断力冠以一种感觉之名”,为的是表明共通感虽也与评判能力有关,却非反思状态中的判断,而是作为结果来看的判断。这一区分既是对二者关系的辨析,也让反思性判断力成为解说共通感的关键环节。正是通过“从自然中的特殊的东西上升到普遍的东西”的特殊路径,理性对自身的呈现遂由“概念”方式改变为“能力”方式。在知识与道德领域中,判断力以客观方式来显示普遍性依据,而在审美领域中,判断力是以主观方式,即通过自身来呈现这一依据。这并非是说,判断力可以替代理性独立行事。在第三批判所提供的特殊判断力中,理性依旧出现于其中,只不过改变了身份,由客观的理性法则转换为主观的理性能力。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判断力从两个方面呈现出共通感获得普遍性的特殊方式。一方面,就共通感作为共同的感觉而言,由反思角度切入判断力可“使我们在一个被给予的表象上的情感无须借助概念就能普遍传达”。这意味着,共同的感觉中呈现的可传达性虽同样也以理性为基础,因而使得这一传达拥有自身的普遍性,但无需概念的方式。另一方面,就共通感作为普遍的感觉而言,其所呈现的是“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的结果”。这意味着,想象力与知性进入一种特殊的关系状态,即“想象力在其自由中唤醒知性,而且知性无须概念就把想象力置于一种合规则的游戏之中”,由此“表象才不是作为思想,而是作为心灵的一种合目的的状态的内在情感而普遍地传达”。
不过,通过反思性判断力消除共通感概念两层内涵中的理性“规定”,只是使其成为先天条件的必要前提,并不足以让共通感承担起作为主观原则的身份。后一任务的完成,尚须将共通感的两层内涵相结合。换言之,如果“情感的普遍可传达性”指向的是与他人的关联,以理性能力为依据,“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呈现的是感性的“可直观性”,以知性能力为前提,那么当康德通过“判断力”获得“可传达性”意义上的普遍性时,便需要以“感性”方式让这一可传达性同时拥有“可直观性”。在《判断力批判》中,这是康德通过纯粹审美判断提出的核心问题,他将这一问题表述为:“一个判断,仅仅从自己对一个对象的愉快情感出发,不依赖于这个对象的概念,而先天地,亦即无须等待外来的赞同,就把这种愉快评判为在每个个别的主体中都附着在同一个客体的表象上的,这种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康德以此表明,如果情感与直观的结合如何可能的问题构成审美领域中先天综合判断的核心任务,那么对这一判断中诸种能力的阐明同时也使得共通感内涵中两种因素的结合成为可能。
在这一意义上,反思性判断力以审美表象方式呈现自身,成为审美判断的意义彰显。正是通过后者,共通感的两层内涵得以通过相结合为整体的方式将自身呈现为主观原则。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不仅对反思性判断力作了重要说明,还将其进一步区分为“逻辑的”与“审美的”两种表象。与“逻辑表象”相比,“审美表象”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指向“一种客观的根据”,而是出自“纯然主观的根据”。因为客观的依据表现为“通过知性和理性来评判自然的实在的合目的性”,而主观的依据则是“通过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来评判形式的合目的性”。两相比较,主观化过程构成关键环节。如果说以反思路径切入判断力时,共通感指向的是自身作为先天条件的内涵,只有在以审美方式呈现这一判断力时,共通感才真正获得自身作为主观原则的身份。在“逻辑表象”中,虽然这一客观化依据已经拥有了感性视角,因而并不等同于“逻辑判断”中的纯粹理性规定,但其与普遍依据的界限并不明晰。“审美表象”则不同,不但立根于感性视角,而且改变了与提供普遍依据的“理念”之间的关系。康德将出现于审美判断中的“理念”称作“审美理念”,表明这一判断既获得了普遍性支撑,又以“象征”方式切断了与客观化理念的关联。消除使分立得以可能的条件,共通感概念中两个要素的结合彰显。在经验论的理论推进中,休谟以彻底主观化的方式审查感性状态,由此呈现出主体自身的情感能力,而在先验哲学的思想探索中,康德通过彻底的主观化方式来关注普遍性依据,由此呈现的则是作为主观原则的情感能力——共通感。
由此康德将与鉴赏力相关联的共通感称作审美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并非是指有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共通感,审美共通感是其中的一种,而是表明只有当共通感是以审美判断为其逻辑基础时,这一概念才不只是一种先天条件,它还以主观原则的方式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身份。康德强调“与健康知性相比,鉴赏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被称为sensus communis(共通感)”,固然着重指向的是“健康知性”与“鉴赏”的比较,将其转换到道德情感同样如此。因为只有在审美判断中,共通感概念中的两个因素才得以通过主观方式结合为一体,呈现出作为先天条件和主观原则的情感。
四、审美视域中的情感呈现:从“合目的性的形式”到“自由的愉悦
从对心灵之情感状态的分析,到对主体之情感能力的探究,共通感概念被确定为审美感受的先天能力,源于新的解说路径的发现。通过反思性判断力所呈现的审美表象,康德既解决了情感能力的先天性问题,也使得共通感概念中的两个因素以主观方式相结合。共通感概念就是在这一结合中成为趣味能力的先天条件和主观原则。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何以需要这一主观原则?18世纪美学思想的探索过程虽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确方向——对普遍性的追问,这一追问的结果却不单纯是理论的旨趣,也有现实的诉求,正是后者成就了情感能力的感性本质。如果说只有通过对普遍性的确认,情感能力才真正呈现为一种现实的情感状态,凭借这一先天条件而再次面对主体的情感能力,也必然会让由此呈现的情感状态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品性。

[德]康德:《康德美学文集》
从审美现象的角度切入,审美情感的具体内容必定处于延展之中,可以在状态和程度上对之不断作出区分。早在18世纪初,艾迪生在美学之旅中面对自然风光体会想象的快乐时,“伟大、非凡或美丽”就成为其表达审美愉悦的主要内容。至1959年,在为“趣味”征文撰写《论趣味》时,苏格兰哲学家亚历山大·杰拉德则进一步将趣味区分为“新奇感、崇高感、美感、模仿感、和谐感、荒诞感和德行感”七种审美感受,并对其在主体中的审美呈现作出梳理。在出版于1764年的著作《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将对审美现象的分析引入“人”自身,虽着重论述的是“人身上崇高和美的品性”,却也由此显示出人的诸多审美风貌。
而从审美感受的角度来概括这些情感呈现,与形貌各异的审美现象相关联的主体感性特质通常被归结为愉快或者不快。休谟从一般人性的总体角度对心理现象进行探查时就对其内涵作出总结:“身体的苦乐是心灵所感觉和考虑的许多情感的来源;但是这些苦乐是不经先前的思想或知觉而原始发生于灵魂中或身体中的。”在1757年问世的《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书中,埃德蒙·柏克以“趣味”作导引,将崇高感与美感接纳为两个主要审美现象,并对其具体感受状态作出心理学分析,认为前者“从属于自我保存的观念”,呈现的是“痛苦忧伤的情感”,后者关联的是“社会特质”,带来的是“快乐或者愉悦”的感受。更重要的是,“痛苦与愉快以它们最单纯、最自然的方式影响人,它们本质上是客观的,其存在不需要彼此依赖”。而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对于美和崇高的探索虽被挪移至先验的基础上,但以“愉快和不快”两种方式呈现的审美感受依旧是康德讨论情感问题的主题和出发点。
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愉快和不快”在状态上的不同和程度上的差异,而在于情感状态以审美方式呈现时所拥有的品质。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将夏夫兹博里认作现代美学思想的开启者有其特定意义。虽然他对“无利害性”原则的确立并不全然与美学相关,客观事实却是,这一原则也成为鉴赏的基本前提。先验哲学时期的康德在对愉快和不快的情感进行分析时,与感官的利害关联也是其首先排除的因素。他认为,“在感觉中使感官喜欢的东西”是“适意的”(vergnügt),而不是美的,因为前者有一种魅力与感动参杂其中,给人带来的是“欢娱”(gratifies),美的事物则是“仅仅让他喜欢(gefällt)的东西”。
不过,排除鉴赏中的利害关联对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来说只是前提,若想获得自身的内涵,还需进一步的条件。在1712年的系列文章《想象的快乐》中,艾迪生通过与感官的快乐、理智的快乐相比较,将审美感受指向想象的快乐,已显示出思考路径的转换。就与感官快乐的区分而言,想象的快乐指向的是一种无功利的快乐,并由此承接了夏夫兹博里的美学原则;从与理智快乐的区分来看,想象的快乐体现出理论的内在诉求,即以何种方式来获得普遍意义上的快乐。《判断力批判》对审美情感状态的剖析沿袭的是这一探索路径,将对愉快和不快的情感的解说置于先验逻辑的体系之上,康德从两个相互关联却又彼此不同的层面,即表象的层面与主观的层面对愉快情感的性质给予分析。从表象层面来看,愉快或者不快就是形式,由此可追溯其普遍依据;就主观层面而言,“形式”就是愉快或者不快,由此可阐明其现实化感受。
从与普遍性依据相关联的角度,康德首先将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指向“合目的性的形式”。这里,“形式”的说法虽难免受古代思想的层层影响,但其解说思路已显示出与这一传统的明显距离。传统思想认为,美的理念作为一种形式来自理性规定,而在近代以来的主导观念中,美的理念作为一种形式则是主体自身表象的结果。在1753年问世的《美的分析》一书中,英国画家威廉姆·荷加斯(William Hogarth)指出蛇形线是“美的线条”或“富有吸引力的线条”时,其关注视角已发生显著变化,曲线之所以更具有吸引力,其实是主体自身想象力自由变化的结果。当然,荷加斯采用的是经验心理学的视角,聚焦的是具体的心理感受。而体系建构时期的康德以先验哲学的视角切入,其关注重心便不是面对外在形式时的具体情感感受,而是形式自身如何通过主体的感受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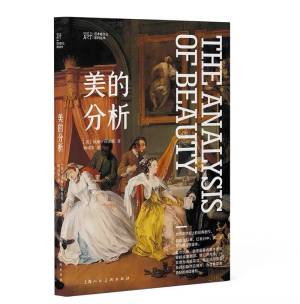
[荷]威廉·荷加斯:《美的分析》
早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将作为感性直观之先天条件的时空形式称作纯粹直观的“表象”,固然是为了与“概念”相区分——后者以知性能力为根据,前者与感性能力相关联,更是意图强调这一“表象”与主体心灵的相关性,它在纯粹先天的意义上是想象力先验综合的结果。到了《判断力批判》,“形式”作为一种感性表象则直接与主体情感相关联,以主观表象的方式存在。虽然在剥离利害观念后,这一主观的表象方式也以“判断”为自身的逻辑前提,因而对“对象的评判”先于“愉快的情感”,但与第一批判相比确已呈现出重要差异。在以时间与空间形式存在的表象中,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受制于统觉的先验统一,因而这一“表象”依旧会以知识形式被客观化,而在以愉快和不快的形式存在的表象中,想象力与知性、理性之间是一种“自由游戏”和“相互激活”的状态,表象正是在这一状态中得以保持自身的主观性。康德由此直接指出,“如果承认在一个纯粹的鉴赏判断中对于对象的愉悦是与对其形式的纯然评判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种愉悦无非就是这形式对于判断力的主观合目的性,我们感觉到这个合目的性是与心灵中对象的表象结合在一起的”。
也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形式在与“目的”相关联时的“合目的性”。在鉴赏判断第三个契机的结论中,康德对此的表述是,“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如果这形式无需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感知到的话”。将对愉快情感的评判与反思性判断力相关联,表明在这一评判中并没有先在的道德法则或自然规则,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目的”,但是通过“判断”的方式,知性与理性又参与其中。康德以“能力”代替“概念”来指称这一判断中的知性与理性,为的是指出,这一判断依旧与目的有关联,但不是指向目的,而是呈现合目的性。“借助于理性而通过纯然概念使人喜欢的东西”真正说来指向的是善,与此相关联的东西之所以“受赏识、被赞同”,是因为“其中被他设定了一种客观价值的东西”。与此相比较,只有“美的”事物才是“无需概念而普遍地让人喜欢的东西”。不过,通过“合目的性”来消弭法则与目的,却不一定通向情感的呈现,它也可通过客观方式与实存相关联,呈现出自然的“完善性”,因为它是“一个概念在其客体方面的因果性”。在这一意义上,将合目的性与“形式”相关联,强化的是合目的性的主观方式。康德指出,“一个关于主体状态的表象,其把主体保持在同一状态之中的因果性的意识,在这里可以普遍地表明我们称为愉快的东西;与此相反,不快则是包含着把诸表象的状态规定成它们自己的反面(阻止或者取消它们)的根据的那种表象”,呈现的便是由合目的性而来的因果性的主观状态。
从审美情感之感性呈现的角度审视,康德进一步将愉快和不快的情感与其现实化状态相关联。表达情感状态的两对关键术语的区分可呈现这一思路的推进,康德将拥有现实性的情感状态称作“愉悦(Wohlgefallen)或者不悦(mißfallen)”,以表明其与“愉快(Lust)或者不快(Unlust)”的情感状态的不同,后者是对情感能力的先验解说,前者是对这一能力的现实呈现。发生这一转化的依据是“兴趣”概念。面对愉悦的情感,康德首先指出,“意欲某种东西和对它的存在有一种愉悦,亦即对此有一种兴趣,这二者是同一的”。由此将愉悦与兴趣相关联,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固然是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状态作出区分,呈现情感的现实化,更重要之处则在于通过兴趣概念引入一种区分,从而获得审美愉悦的特殊品性——“自由的愉悦”。
在与兴趣相关的意义上,康德将愉悦区分为三种现实化方式:“偏好”(Neigung)、“惠爱”(Gunst)和“敬重”(Achtung),其中,惠爱作为呈现审美感受的愉悦是“一种没有兴趣的和自由的愉悦(freie Wohlgefallen)”。这里,将审美愉悦与“自由”相关联显然有其特殊指向。回顾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自由首先以与理性相关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呈现,如果说先验意义上的理性自由还指向的是消极层面的内涵,即摆脱感性的干扰,那么由实践理性而来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则是由自己来规定。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一旦感性存在也需要与自由相关联,势必意味着这一感性是由理性来规定的感性,意志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获得自身的自由。然而从第三批判开始,自由的内涵发生了反差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理性的感性意义上的自由。当然,为了获得普遍性,感性意义上的自由也会与知性、理性产生关联,但后者却不是作为法则的知性、理性,而是作为能力的知性、理性。因而,自由的呈现便不再是由知性、理性法则来规定自身,而是想象力与知性、理性能力之间的一种自由协调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强调“惠爱是惟一自由的愉悦”,就意味着自由的评判标准已发生变化,从是否由“理性”来规定到是否与“兴趣”有关联。

[德]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康德认为,适意的事物会带来欢娱,在于构成其基础的兴趣呈现为“偏好”(Neigung),善的事物能带来赞同的感受和愉悦,表明构成其基础的兴趣呈现为“敬重”(Achtung),而美的事物之所以让人单纯的喜欢,则源于构成其基础的兴趣呈现为“惠爱”(Gunst)。差异之处在于,前两种情感都内含着兴趣,适意建立于对感官的兴趣,善通过兴趣与概念相关联,产生出对道德法则的兴趣,而惠爱则是全然没有兴趣的,它既不建立在兴趣之上,也不产生出任何兴趣。回顾18世纪的思想发展,将感性自由的判断依据指向“兴趣”概念,虽是对英国经验论“无利害性”观念的承接,但康德无疑有着关键性推进。前者想要排除的只是与感官相关联的“利害”,而康德的“无兴趣”则不只是要剥离情感对感官的依赖,更是要去除理性对感性的规定。值得关注之处恰恰在于后者:通过对共通感概念作为先天条件与主观原则的解说,康德引出了审美领域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也由此呈现出对待理性的一种矛盾态度。不过,“矛盾”的呈现只是一种表征,如果说在审美愉悦中我们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理性,那么恰恰是在对后一种“兴趣”的去除中,一种新的兴趣内涵已蕴含其中。康德在“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中对这一新的兴趣概念——理智的兴趣的解说,是这一思路推进的结果。
与新的兴趣概念相对照,美的分析论中的兴趣概念承担的充其量只是消极功能,即通过排除自身,而剥离其他因素对情感的规定,由此获得的“自由的愉悦”,指向的也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尚无进一步的内涵规定。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康德将这一愉悦的内在状态指向“静观”,认为与此相关联的“鉴赏判断纯然是静观的(kontemplativ),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一个对象的存在漠不关心、仅仅把对象的性状与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加以对照的判断。但是,这种静观本身也不是集中于概念的;因为鉴赏判断不是认识判断(既不是理论的认识判断,也不是实践的认识判断),因而也不是基于概念,或者也以概念为目的的”。后来的研究者之所以会对康德的审美“静观”理论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只关注到康德在美的分析中对愉悦内涵的解说,而忽略“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部分在谈及兴趣概念时所发生的变化。第42节重新面对兴趣概念时,康德发现并阐明了一种对美的直接的、理智的兴趣,并认为“他不仅在形式上喜欢自然的产品,而且也喜欢这产品的存在,而没有一种感性魅力参与其中,或者说他也没有把某种目的与之结合”。从这一兴趣也被称作“自由的兴趣”可推知,康德其实提出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的愉悦”。消极意义上的愉悦主要目的是排除外在的规定,在积极意义上,自由的愉悦则不仅伴随于“形式”中,且与“产品的存在”相关联,并通过后者内含的创造性维度彰显出愉悦的“自由”本色。
原载:《外国美学》41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4。
来源:外国美学公众号,2024.11.15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













